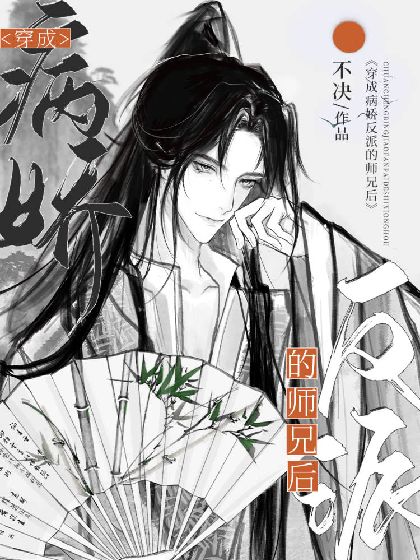正月十五那天,长春又下了场雪,屠老七站在冰面上,看着湖对岸的小村子,村子里的烟囱在冒烟,这家肯定是在煮汤圆。
他咽了咽艰涩的口水,他叔正在凿冰。
“叔,干完这一笔,咱们能不能回老家不干了?”
屠老五像是没听到侄子的问话,只顾把冰面凿得震天响。
老七握着手里的铁锹,又问:
“叔,我们这么干,凡叔能不能怪我们?”
凿冰的人终于抬了头,老五抹了把通红的脸,开口就是埋怨:
“你光站着干什么!赶紧帮着我铲,等会儿有人过来了怎么办?”
老七吓了个哆嗦,赶忙低头往外送冰碴,老五这会儿倒是停手了,回头向身后望,几米开外的冰上停了辆面包车,老凡头在副驾上坐着,脸没朝向这边。
“你凡叔平时不说话,其实心里都跟明镜似的,出了这事谁也不愿意,他不会怨咱们的。”
冰面比地上冷,老五说话的声音像是冰疙瘩掉进了水里,围巾上的哈气不至于冻上,只是湿答答地往他嘴上捂,老七埋着头铲冰,有一下没一下地吸鼻子。屠老五把围巾在脸上围了两圈,又向肩膀后一甩,侄子忽然又抬了头。
“叔,我刚说的干完这一笔不干了,这是真话,我真不想干了,我想回家去娶方慧。”
老五的脸被围巾蒙了个严实,只剩两只发红的眼睛在外面,他上下扫了侄子一眼,随着铲冰的声音重重叹气。
他总这样,一块儿在长春打了十年工,老七永远都读不明白他叔在想什么。
虎口被震得发麻,铁锹在他手里转了又转,最后他还是选择给当叔的一个台阶下。
“我知道你总不想听我说话,叔,你要实在不想听,我就唱首歌吧。”
这次老五压根儿就没停下,一副他侄子不存在的样子,脚底的冰面铲了差不多一尺深了,水的影子都没看到。老七猛吸了一口气,抡圆胳膊向外铲冰,嗓门一开就唱起了歌:
“谁家的,爷们儿啊,藏进下午碗架柜儿啊,你红啦,我绿儿啊,还骂我没出息儿啊——”
感情充沛,但没一个字在调上,声音随着他挥铲子的动作断断续续。
唱了几句,老七唱来了劲,铲子向着冰里一插,嘴里喷出的白汽和远处的烟囱交相辉映。
“我活着是你的人儿啊,死了是你的鬼儿啊,你想咋地儿就啊咋地儿啊——”
“你他妈有完没完!”老五怒吼一声,手里的冰锥飞出去好几米,在冰面上打了四五个旋。
老七顿住了,白汽像是锅炉断了柴火,戛然而止。
“叔你什么意思啊,我凡叔都要自己一个人上底下去住着了,我就不能给他唱两句送行吗?”
“你唱的这是送行吗?我看你是要把我俩一起送进去!”
老五一把扯下了蒙着脸的围巾,肘子色的脸上怒目圆睁。
老七躲着他的视线,嘟囔着用铁锹拨弄坑里的碎冰,小声顶了一嘴:“我就知道你和厂长是一伙的。”
冰面上的北风在刮,老五眯上眼睛侧过脑袋,问他:“你说什么?”
“我说你跟厂长是一伙的!”
喊完这一句老七就卸了劲,叔侄对着,两人嘴里的白烟此消彼长,老五回头望了一眼被自己扔出去的冰锥,接着猛地低下脑袋,开始脱脚上的棉鞋。
“我他妈叫你唱,叫你唱,你接着唱啊!”
棉鞋砸到了老七的后背上,打得他一趔趄,老五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追,蹦着去脱另一只脚上的鞋。
“我他妈——”
第二只鞋还没脱下来,老五的身子后头就响了一声,这动静是在冰上走的人最怕的——清脆悦耳,如同清泉流水——是冰面碎裂的响声。
这一响俩人都停了,老五先回了头,他向脚下看,裂的不是他们脚底下那块,他又抬起脸,也不是刚才凿的地方,再往远处瞅,面包车的车头向下沉了一尺,车轮边是潋滟的水光。
车里的人依然在向着另一边望,叔侄俩的大呼小叫都不能让他为之所动。
一声短暂而干脆的水响,车头彻底没入了冰面下,老五木然地摘了头上的雷锋帽,脑袋上是被焐出来的热乎气,身后那该死的混小子砸吧了两下嘴。
“凡叔,你怎么自己先走了?”
——
四十公里外的长春市中心,尤天白坐在一辆同样是银灰色的面包车里,车外是别墅区的白砖墙,一个穿着风衣的保安站在保安亭里,目不斜视,一丝不苟。
尤天白把车窗开低了些,向外弹烟灰。
车已经在门口停了四十分钟了,没进去门,等的人也没出来,将近一个钟头的时间里,只有门口的保安和他做伴,荒度寂寥时光。
确切来说不是做伴,是尤天白单方面搭话,小保安从始至终没开过口,即使面包车里的男人向外弹了十五六次烟灰。
想到这儿,他又弹了第十七次,顺便把烟屁股也扔了出去,视线回到车里,再次拨通手机屏幕上的号码。
号码主人的事,要从两年前说起。
二零一七年,二十七岁的尤天白因为一些说出来丢脸的个人原因,从北京回了长春,这是他当了三年兵的地方,和北京比起来,有种原始的安心感,他用在北京开大众浴池赚的钱租了一个铺子,买了辆二手面包车,干起了不完全的老本行。
老本行指还是民生行业,不完全是因为稍微转了业,具体点说,从澡堂子转向了销售,再具体点,卖成人保健品。
店外白雪皑皑,店内霓虹闪烁,作为殡葬一条街上唯一一家24小时营业的成人用品大全,他的生意实在没什么红火可言。不过好在店开在技校后身,一些半夜光临的顾客也算照顾了店面,只是顾客不一定是成人。
不过尤天白不在乎这些,他乐在其中,即便每年开春前都要跑到黑龙江边上去进货,他也哼着歌乐此不疲。
但今年情况有变,全都是因为正月里在连着下雪,下雪意味着道路结冰,意味着车胎报废,意味着在休息站边小饭馆吃饺子的美好时光,通通化为了在车屁股后推点不着火的五菱宏光。
这可不行,尤天白打开了常年没有新帖的同城论坛,发布了一条没有技术性和吸引力的“招学徒”,不抱希望了一个星期,终于在两天前,他收到了一条简短的私信报名。
报名人留了手机号和地址,号码主人就是他现在正找的,地址就是他现在正停的。
所以为什么住在别墅区的人会当性保健品店的学徒?
尤天白又叼起了一支烟,听筒那边还是没人接听,他选择把头探出去,重新看向陪他一起蹲了一个小时的小保安。
“能不能进门”,“能不能叫人”又或者“能不能关了电让我自己爬墙”,这些话尤天白都问过了,在他思索自己的北京口音是不是在东北显得太过生分的时候,一个更合理的问话冒了出来。
“我说,”他把胳膊和脑袋一起钻出了车外,“你下班后我能约你吃顿饭吗?”
小保安终于有反应了,他脖子一抻,鼻子喷出两股白汽,这让尤天白想到了打不着火的拖拉机或者是田埂上的牛,这让他很开心。
可他爽朗的笑声还没超过一秒,就被一道从柏油路尽头奔来的黑色打断了,引擎声混着石子的弹响,黑色如同一条养在水潭里的生动游鱼,直接插在了面包车和保安亭之间。
扑面而来的是大马力发动机的热气,尤天白眯着眼睛压低视线,嘴角的烟静悄悄地烧断了一截。
这可不是普通的黑,这是掐零取整价值四百多万的黑,各种参数他不记得了,只认得法拉利,至于价格,他买不起所以数了下零,对四百万记忆颇深。
尤天白承认,从刚才开始就赖在别墅区门口不走,一部分是不觉得留言的是骗子,另一部分是想看看这市中心的田园别墅区能开出什么花来,没想到第一朵就开出了一辆法拉利F8。
引擎声停了,车门打开,驾驶室下来的人背对着他,只能看到砂金色的头发。
保安总算动了地方,他微微弯下身子和车主低语了几句,接着把眼神投向这边,上午十点的艳阳里,砂金色头发的人终于肯转过头来看看他了。
对视的一瞬,刚刚停下来的引擎声又轰鸣了起来,只不过这次是在尤天白的脑子里,从左耳到右耳,再从右耳回到眼前,他嘴里的烟又烧掉了一截。
真浪费,他这么想着,还是没去吸。
东北,作为中国最靠近西伯利亚的地区,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养出了一批批身高腿长又中看的年轻人,尤天白当然看过不少,他没有盯着别人看的习惯,也没什么老牛吃嫩草的癖好,但是眼前这个,他甚至舍不得转开眼睛,然后再若无其事地来看第二眼,他就这么一直盯着,盯到那人彻底转过身来,用琥珀色的眼仁直视他。
更可怕的一点来了,他发现这帅哥长得很眼熟。
同学?他明显跟自己差了辈,战友?同理,差辈,多年不见的朋友?如果真有这么显眼的,他不可能记不得。既然以上几种都不成立,那就只剩一种可能了。
帅哥冲着这边来了,尤天白赶紧从冥想恢复到了社交状态。
“你好你好,”他在车里抬起一只手,先打了招呼,“我在想,我们是不是以前在哪里——”
睡过。
如果是对别人,尤天白一定就直接这么问了,但面对着眼前如此合口味的一张脸,他居然说不出口。
金头发停下步子,低头捡刚被扔在地上的烟头,反手丢进了垃圾桶。
哟,还挺有素质,尤天白一时有点不好意思。
帅哥转过身子,和还挂着笑的他四目相对,接着一拳抡在了他的脸中央。